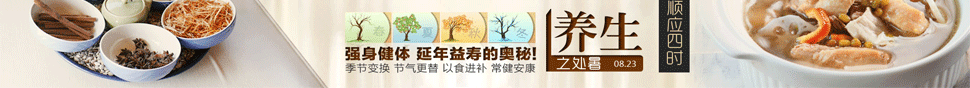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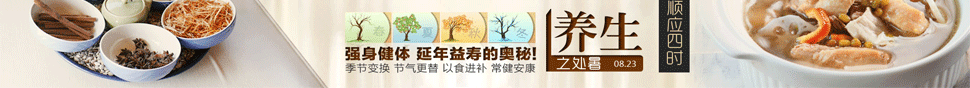
很多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黄金年代,有理想,有自由,天才辈出。九朝古都洛阳一所没啥名气的学校,学生读书之刻苦,志向之远大,生命之昂扬,现在的河大、郑大的学生看了,恐怕也要汗颜!
张冲波
文
年恢复高考的第四年,国家刚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,我有幸应届高中毕业就跨入1951年建校的洛阳林校,我是幸福的。正如当时的流行歌曲所唱“我们的生活,我们的生活,比呀比蜜甜”、“幸福的生活充满着阳光,充满阳光”。
洛阳北靠邙山,南临龙门,是一座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,素称“九朝古都”,先后有夏、商、东周、北魏、隋、唐等十一个王朝在这里建都,长达1529年。在隋唐盛世,洛阳人口百万,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。洛阳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,东方红拖拉机厂、洛阳浮法玻璃厂、洛阳轴承厂、洛阳矿山机械厂、铜加工厂闻名中外。我有幸在九朝古都洛阳求学,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无形中熏陶着我,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,我倍感自豪和骄傲。
多年之后,我和同学们相聚,重返母校参观。
站在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前,那个床位,还是靠窗。王东学那时长得又白又净,但每夜总是最后一个上床。因为他长得白,若是早睡,同学们都撩逗他,三番五次摸他的光身子;乔华爱睡懒觉,故意把宿舍的开关绳挽起来,让每天查铺的矮个子老师够不着。现在里边已经不住人了,只当文物古迹摆在那儿,让一拔又一拔的校友前来凭吊。据说五十年代的老校友,如今已白发苍苍,坐在床头比划着,说到动情处,热泪盈眶,一片唏嘘,比我们还激动。这大概是另一种青春祭吧。
走进教学楼,旧式三层楼,红砖青瓦,古朴典雅。当年的紫荆树、木槿树还在,那从早春到盛夏永远开不败的紫红的木槿永远留在我的脑海。从门缝里瞅一眼曾经的教室,还是那般幽静,课桌仿佛还是过去的模样。
那次,教育种学的张妮娜老师,面对上课有人做小动作,她做了一番解释:“别的班有女同学,课堂秩序非常安静,就是地上掉个针,都能听见。而你们班没有女同学,是和尚班,所以就多配了几个女老师,但还是不顶用。”张老师个子高挑,面容娇好,举止端庄,双眸生辉,语气柔和。她的板书和她的人一样漂亮洒脱。
我和同学私下称她“美人胚子”。她的爱人李老师,大高个子,教我们林业机械,我非常感兴趣,什么化油器,什么活塞运动呀,等等。后来他当上了副校长。这次校友聚会,夫妻俩都来了,现已老态龙钟,李老师步履蹒跚,张老师瘦小嬴弱,老年斑显现。但我依稀可见她二十年前的美妇风韵。
一年级时,我们的教室在三楼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窗外鹅毛大雪,教室里暖暖融融。教气象学的女老师,拖着长腔,一板一眼地传授;教化学的女老师,戴一副近视眼镜,语速极快,倒背如流;教微积分的男老师,嗓音略带沙哑,面带笑意,头扬得很高,一半时间瞅学生,一半时间瞅天花板,飘忽不定的样子,教学却水平很高。就连我这个对数学不感兴趣的人,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记得二年级时,上造林课,老师讲得津津有味,而我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大一会儿,被同桌推醒。王老师问我:“春天里下的霜,是早霜还是晚霜?”我略加思考脱口而出:“晚霜!”王老师伸出大拇指,称赞我说:“聪明!绝顶聪明!”引来哄堂大笑。
我们来到餐厅旧址前,门前的两棵冬青树还在,只是更粗更壮。绿色的冬青花发出淡淡的香味,似乎能找出从前的感觉来。只是现在变成了办公大楼,窗明几净,巍然气势。想当年,每份素菜5分钱,每分肉菜1角钱,2两馍5分钱,一份卤面、炒面也是5分钱,一天5角钱、一月15元足足有余。那时助学金每人每月10元,我家庭困难,班主任是灵宝同乡,照顾我吃一等助学金,每月12元,加上家中每月补助10元,绰绰有余。
我那时喜欢在街头买报纸看,如《中国青年报·星期刊》、《羊城晚报》及《新观察》等。我和李汉章坚持吃咸菜,吃豆腐乳,每天省一角钱,一月就省3元钱,就可以买每张4分钱的十来份报纸。当时《诗刊》2角,《人民文学》2角8分,《新观察》2角等。
我购买的第一本综合性杂志是半月刊《新观察》,记得第一期封面是姜昆、李文华说相声照片,还有一期是张瑜在《知音》扮演名妓小凤仙的照片,那期卖得很快,封底是王心刚骑马一身戎装的蔡锷将军扮相。
《新观察》吸引我的是社会调查类文章,基本期期买,参加工作后,还动员林场单位订了一年。后在一九八九年《新观察》停刊。徐刚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伐木者,醒来》整刊篇幅刊登,轰动一时。就此我曾给徐刚致信,让杂志主编转信,后因故耽搁,至今想还是一桩憾事。
我买的第一份报纸是《中国青年报·星期刊》,还有《讽刺与幽默》等,从此阅报买报是我课余、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,二十多年兴趣只增不减。后来我每次出差,都要购当地报纸藏之,各种各样不下百种。
杂志、报纸均在老城商场马路斜对面的售书亭,售报是个中年人,胖胖的圆脸,稍谢顶,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现在还能记起他的模样。
记得那时还常在街上买《羊城晚报》,当时每天一份四个版。主要是看《花地》,徐刚的散文多在上边发表,好象《诗海泛舟》也在此登过。印象最深的是短句随笔中黄药眠的一句话:世界多么悲观,人一生下来就向死亡线上奔跑。
还有一篇外国小说译文,讲的是一群探险者在森林里迷路,半个月突围不出来,弹尽粮绝,都面临生死边缘。一老者气息奄奄,临终之机,交给其余4人一保险箱,沉甸甸的,上有锁。嘱托他们,不允许他们四人随便打开,有权利打开的是跑出森林的人。这时四人又开始突围,有两个实在顶不住,想一死了之,但又一想那保险箱的宝物在等待着他们,再有几天行程就可胜利了,就咬牙又继续走。当4人精疲力尽,走出森林而获救后,才共同打开保险箱,一看他们惊讶了,原来竟是一块石头,大多失望颓废地瘫在地上,大骂老头是骗子,他们上当了,而他们恰恰忘了,正是这块石头,让他们心存希望和信念,支持着走出大森林,走出死亡地带。换回的是一个个活鲜鲜的生命啊!二十年了,此小说宗旨我铭记在心。
这次聚会才听说,班长张克清深夜还偷过学校食堂的大白菜,拿回宿舍用盐腌了吃,来省伙食费。那时,我父亲承包生产队果园大丰收,经济条件相对较好。记得年夏天,我嘴馋,学生食堂天天煮没有油水的茄子吃,很倒胃口。当得知有病可以吃小灶时,我就跑到校医务室央求医生给开了个病条,终于可以吃炒菜了,吃上有油腥的汤面条了。
我们来到操场边,昔日偌大的操场已不复存在,被新的教学楼代替。那四周翁郁葱茏的法国梧桐依稀存在梦中。那年中国女排刚获得三连冠,我们在课余时间就大练排球。记得那时学垫球、传球,手腕整天被硬绑绑的排球打得通红通红,而学“铁榔头”郎平扣球手掌更疼。
记得说话有点结巴的张俊昌同学,翻跟头的动作很滑稽,总是翻到中间,双腿并立直直的,上不来下不去,脖子憋得通红通红,需要人帮忙翻一下。这次同学见面还取笑他。
还有一件滑稽事,年冬天我到老城商场买帽子,已挑好了57号尺码的,正准备掏钱,这时一位中年人也来买帽子,他要的是59号的,一问价钱和57号的一般多。我心想,大两号也是1元5角,小也是这个价,还不如买个大的,占便宜。谁知戴个大号帽子,跑操时,风一吹,帽子就掉,让我很恼火,很尴尬。
我们徜徉在图书馆楼前,当年借阅图书、翻阅阅杂志十分方便。我先后借了几本中外小说,有《桥隆飚》、《第二次握手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高老头》等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高老头临终时,对他的三个女儿所说的:“你们不是来看我的,是看我手里攒的钱呢!”记得那年冬天我买了本《小说月报》,上面刊载有张一弓的中篇小说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我缩在操场南边的一个土堰下,在冷冷的寒风里,看得热泪盈眶,心血澎湃。
我平生的第一首诗是年春天写就的,具体是那一首,一点也记不起。可能是《保险丝》吧,每当危险来临/你就啪地一声融化自己/保住大家的平安福气。可能是《纽扣》吧,小小纽扣/谁也少不了你。起初是很稚嫩的哲理诗。从此一发不可收,每天都有一两首,最后投寄给河北沧州的《无名文学》,当然是退稿信。
有一次竟被班主任李当彬发现,他另眼看待表扬了我,从此改变对我逛皮的印象。我第二次去洛阳博物馆参观,又写了许多咏物诗,赞叹人类祖先的神奇和文明。这一年的暑假,我写了组诗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投给刚创刊不久的《洛神》,当然还是退稿信。但我矢志不移,若干年后写出了几首满意的诗,这是后话。
这一年的暑假,我回到家乡,感到农村改革的变化、大集体在这一年土崩瓦解,分田地、分牲口,搞单干不亦乐乎。我写了一篇小小说《分牲口的故事》。讲的是田地分了,而集体财产牲口也快要分了。同时还写了一篇散文《芝麻开花时节》说的是大集体小伙伴恶作剧偷吃芝麻、队长种芝麻遭贬,后来实行责任田,芝麻遍地是,生活富裕了。
九月寄给《灵宝文艺》,很快收到编辑任化民的来信,说《分牲口的故事》反映是现实,但这方面是政策问题,还没人写,不能登,而《芝》文生活气息浓,拟在11月刊登,随后如期寄来样刊,我非常高兴。年11月《灵宝文艺》发表了我的处女作品《芝麻开花时节》,载入了我文学创作的里程碑。
洛阳林校不是什么名校,也没有过多的人文资源。但,她是我们每个人事业的一块跳板,人生的一块基石,是我们从烂漫少年走向茁壮青年一个必不可少的桥梁。在这里我们吸收了营养,在这里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。此后,人生磨难、职场挣扎、事业困顿,接踵而来。青春的彷徨、命运的无情、中年的无奈,人生悲喜剧轮番上演。
(内容编辑:谷乐图片来源:网络)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